当新水墨的需求泡沫被刺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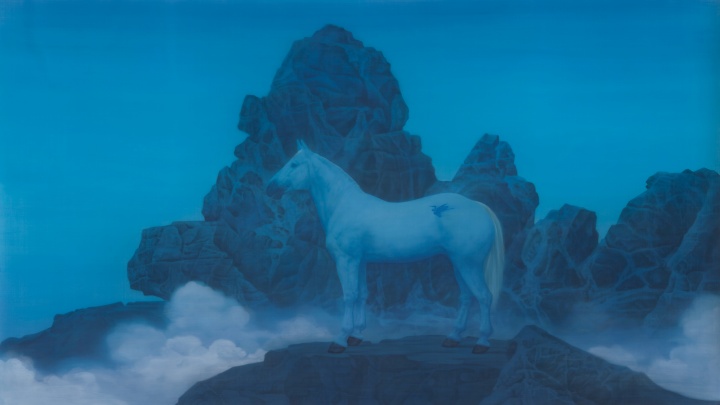
如果说到艺术圈存在同中国经济一样的产能过剩问题,那新水墨板块还存在同外部大环境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速度。
就像朱小钧回忆到的一样,在中国艺术市场如日中天、高潮迭起的2011年,新水墨是沉寂的:“展览屈指可数,都是大家凑点钱就把展览实现了,基本上也没有买卖,最后留几张画给主办方就可以了。”而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下滑,新水墨作为本身也在不断自我发展的艺术版块,在国际拍卖行的“挖掘”下,迅速成为了艺术市场中资本的囊中之物。
新水墨作为同中国当代艺术同期开始发展的发生在中国传统绘画领域的艺术革新,已经有了三十年颇为完整的且没有受市场过多干扰的自身逻辑,并出现多位具有典型代表的艺术家,且和中国人存在着天然的文化共鸣。这些都为新水墨被市场认可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新水墨也就不无道理的迅速“走红”,艺术家价格也迅速窜高。徐娟永远记得在某次博览会上,刚挂出的一张画就有四拨人围过来要求购买,彼此之间互相竞价不停加价的气氛俨然一场竞争激烈的拍卖会。她并没有在其中看到“钱景”,而更多的是恐慌。果然就如同每个亲历过新水墨市场的参与者都会有的感受一样,“不愁画卖,只愁没画卖”的时间只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市场便嘎然而止。
新水墨这场中国速度般的大跃进中,最典型的就是朱新建,2014年年初全国各地拍卖行的朱新建专场加起来不下30场,而到2014年年底成交率几乎已经降到了50%,到2015年初,朱新建已经成为了艺术市场上曾经存在过的一道风景。这其中或许有艺术市场遭遇外部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歹势,但朱新建绝不是水墨市场的个案。2016年春拍香港苏富比专场多位重要水墨艺术家的市场遭腰斩也只能足够说明问题:新水墨的持货人绝大多数都是行家而非真正的藏家;行业内的快速流动带来了市场的膨胀但并没有带来市场的真正扩张;水墨产量高的特点也让持货人迅速满仓……但归根结底,对待艺术品非正常的、非理性的消费态度导致了市场的过剩。而甚至在杭春晓看来,问题更深层的原因是在艺术市场中对新水墨的消费需求还没有达到的时候,经纪单元对水墨价值的过度鼓吹制造了这场“需求”的泡沫。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
微信号:hiartmimi
(可享会员福利)